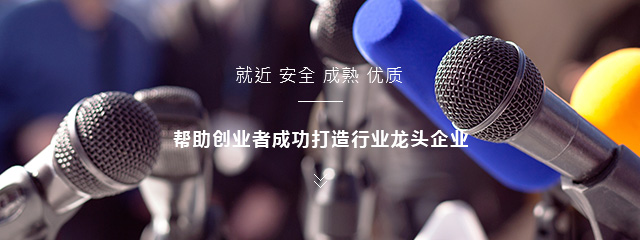我在故宮修家具����,天橋奇遇“高人”�,小木匠煉成古典家具修復師
40年前����,蹲在北京天橋底下,等待接活的小木匠吳永忠,怎么也不會想到�,自己有一天能親手拆開故宮里“皇帝都沒拆開”的箱子�。
那是吳永忠“北漂”的第一天�。他是個農村孩子,出生在安徽皖南池州山區,吳永忠是家中五個孩子的老大,為了供弟弟妹妹上學,高中沒讀完就輟了學����,和本鄉的一位木匠師傅一起去北京討生活��。
“沒想到第一天就進入了明式家具的行當。”
被一位行業內高人帶進圈子以后�,吳永忠歷練十年�,不但成為了安徽東至古典家具協會會長�����,開起了自己的古典家具行����,還成為了淘寶“極有家”上����,一家中式家具店的技術指導���,讓瀕臨失傳的手藝得以延續����。
北漂木匠的逆襲
有點兒像武俠劇中的情節,那天���,一位須發皆白的老先生路過天橋,把兩個小木匠帶回家里做活���,修家具,其中一個就是吳永忠��。
后來吳永忠才知道�����,這位須發皆白的老先生�,姓趙���,來頭可不一般���。
日軍占領北平時期,曾抓這位趙先生到營房做伙夫,由于經常和被俘的外國士兵接觸�,趙先生奇跡般地掌握了六門外語���。幾十年過去以后����,趙先生在北京朝外市場開了一家古典家具店�����,專門和外國人做生意。
那天一進院子���,吳永忠就看出來,院里的可不是一般的家具��,而是顏色古舊���、劃痕斑駁的明清老家具����,有的缺了個腿,有的榫卯結構松弛了��。
就在這間院子里�����,吳永忠和人生的第一位老師趙老先生學起了修復明式家具�,從拆散��、修配家具開始�����,到打蠟、燙蠟���,熬制膠液,吳永忠白天勤快地干活��,晚上則在民房的席子上畫圖��,學習明式家具的結構。
吳永忠回憶�����,那時的“北漂”遠比現在更苦�。民房沒有自來水,吳永忠總是在前一天晚上儲一盆水,寒冬來臨之后�,這盆水會結一層薄薄的冰�����,每天早上,吳永忠要鑿破薄冰,用刺骨的冷水洗漱����,再早早趕赴北京的朝外市場����,用“現學現賣”的英語和外國人討價還價��。
改革開放不久的八十年代����,大量外國人來華購買古玩文物��,而如今幾十年過去�����,富有起來的中國人又將許多當年外流的古玩文物購買回國。這些古玩文物們不但見證了千百年間的風風雨雨����,也成為了新中國富強的見證��。
那時,吳永忠已經換了個東家,在古典家具世家子弟梁廣平先生的廣漢堂幫工��,梁先生見這個小木匠干活勤快�,還自學了英語,就經常帶著他談生意。
有幸能看到老板和兩個合伙人馬未都�、張德祥先生環坐談話��,吳永忠經常一邊旁聽,一邊學習,偶爾遇到自己辨別不清年代的家具����,就向幾位大佬請教���。久而久之�����,吳永忠自己也有擁有了一雙巧手、一雙慧眼��。
入行十年�,當年的小木匠終于熬成了行家里手,在北京的呂家營開了一間自己的門店����,名字叫做“永興堂”�。
這些年�����,錯過了許多個億
從1989年開店至今����,吳永忠已經過手不下千件明式家具�����,他曾戲言,已經錯過了不知多少個億�。
從八十年代末至今����,一件普通明式家具的價格能翻上百倍�,難得的珍品則可以翻上千倍。而北京市中心的房價在這三十年里也不過翻了三�����、五十倍���。
吳永忠曾收購過一對明代黃花梨木的椅子�,3萬元的價格收進來,在手里放了四年����,以50多萬的價格賣掉了����。如果放在現在�����,恐怕還可以賣出更高的價格���。
“我是一個生意人��,不是收藏家,有時候明明知道東西還能升值����,但是來了買主��,也得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!”
互聯網興起之前��,賣古典家具這行最講究的就是“速度”。小販在地方收購到家具以后���,會給北、上�����、廣的店鋪掌柜們發消息����,想要的人會趕緊帶著現金趕赴當地看貨,一錘子買賣����,沒有反悔��,全憑眼力。
吳永忠主要經營蘇作家具�����,因此在江浙一帶奔走得最多�����。為了拿到好貨��,經常在半夜收到消息以后馬上趕往機場�,每次都是只身帶著銀行卡前去,回來時拉著滿滿一車家具。
家具一運到北京,收藏圈子內的老主顧們就會聞訊前來觀摩�,有誰看中了某款家具���,就在家具上用筆寫上自己的名字����,還沒付錢�����,這件家具就屬于他了�。王剛����、張鐵林等文化名人是永興堂的常客����。
“收藏圈里的人都很講信譽����,一旦預定基本上沒人反悔����,所以基本上都是‘先看先得’。”
被小販設局
混跡古典家具圈數十年,吳永忠早已練就一對火眼金睛���。即便如此,在年輕時也曾交過不少“學費”。
地方收家具的小販經常會給門店老板們“設局”��。
曾有一個山東濱州的小販請吳永忠去看一個“明代的”黃花梨案子���,據說是當地一戶農民在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年代從大戶人家分來的�����。吳永忠在那天中午就趕到山東濱州,想下鄉去看貨的時候,小販卻說農民白天要干活��,晚點才能過去����。
經過一片片荒郊野地,吳永忠抵達時已經是薄暮時分�����。當他在那間光線昏暗的小土房里借著白熾燈的光仔細觀摩時,忽然燈光熄滅,全村一片黑暗��。
那個農婦用山東口音的普通話解釋說��,村民為了省電���,商量好了在晚上10點以后就統一拉掉電閘���。吳永忠只好掏出手電一寸寸地觀摩���,雖然沒看出哪里是假的��,卻也不太確定。
這時身邊那個小販又開始煽風點火,說第二天一早還有人來看����,如果確定不了��,第二天可能就是別人的了。思來想去�,吳永忠當晚就付清了錢款����,帶著案子連夜離開了這座閉塞的小山村�。
人和貨都抵達北京以后�,吳永忠發現了問題——案子的邊緣在運送過程中磕出了一道小小的裂紋,而這條裂紋之下分明露出了黃色的木頭����。放置幾百年的明朝家具會有一定程度的氧化����,木質發黑�,露出的黃色的木頭證明了案子是現代高手的仿制的。
“我們這行都是一手交錢�,一手交貨��,你看錯了,說明技不如人�����,沒辦法找人家�。”所以幾十年以來,吳永忠一直在修煉自己的道行��,也在磨煉修家具手藝��。
我在故宮修文物
從故宮運送到首都博物館的木箱子貼滿了封條�����。
那是幾百年來,掌管皇家府庫的官吏親手貼上的��。這些木箱里裝著的���,是清朝皇室的備用家具��,官吏們每清點一次,就要在木箱上多貼一道“某某年某某人清點過”的字條�。
皇帝使用的每一件木家具����,都會由民間的能工巧匠做兩套�����,以便于損壞之后及時補上����,這些木箱子里的���,就是備用的那套��。
這些備用家具中有不少從康熙��、乾隆年間就一直被塵封��,吳永忠作為首都博物館的古典家具修復師,親手見證著時隔幾百年的“開箱”���。
拆開塵封幾百年的箱子以后,里面的桌子����、椅子光潔如新���,絲毫沒有劃痕�����。但其實只需稍稍一碰,榫卯結構就會松弛��,因為當年上的膠已經早已風化����、脫落����。
為了讓這些文物能成功展示,必須要重新上膠。吳永忠介紹�����,這種膠是使用豬皮膘作為原料�,用一種特殊的工藝熬制而成的。
過去,手藝傳男不傳女����,加上最近幾十年來傳統文化凋敝��,目前,能用這種手藝修復古典家具的人,全國也只剩下了幾十個���。
接手修復故宮家具的活計純屬偶然。
首都博物館的館長王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,經常光顧永興堂,與掌柜吳永忠閑談的時候,說起了有一批從故宮運出來的家具,沒人能修復����,并深表痛心遺憾��。
吳永興有幾十年的手藝傍身,于是主動請纓��,就這樣在2002年成了首都博物館的古典家具修復師���,前前后后一共修復了上百件故宮家具��。這些家具還陳列在首都博物館的圍欄里����。
吳永忠說�����,近百年來,被運出國外���、被毀掉的文物不計其數,國內剩下的這些�����,需要我們好好保護��。
新中式��,不如原汁原味的明式家具
如今,吳永忠的案頭總是堆疊著一些“新中式”家具圖紙����,那是由清華��、美院的學生設計的,請他批評指正�。吳永忠坦言�,這些“新中式”的設計圖中,十有六七是結構不合理的。
作為古典家具圈子的“老炮兒”��,吳永忠對近幾年年輕人喜歡的“新中式”家具頗有微詞�����。他說�����,新中式雖然好看���,但很多家具的結構設計不夠合理��。
而明式家具不同����,它是文人士大夫們不斷地設計��、改良�����,經過幾百年沉淀下來的經典款式,無論是結構還是審美�,都足以傳之后世��。
“簡單地說吧,‘新中式’家具放個幾百年���,可能就不能用了;即使能用����,后代人也不一定會接受這個審美�。”
收家具幾十年后��,吳永忠發現�,似乎從2010年開始��,收上來的好家具越來越少了����。
近20年中國到處在搞拆遷���,之前往往是拆一批�,就有一批古董家具浮出水面����。隨著老房子越拆越少,老家具也就越來越少了。
窮則思變,吳永忠在淘寶上開了一家明式家具的專賣店,樣式是他根據幾十年的積累一比一復制出來的,由于不是古董�����,不會賣到明式家具的“天價”���,能讓普通的古典家具愛好者也使用得起�����。
吳永忠還在一家入駐“極有家”的中式家具店擔任技術顧問�。這位店主是個年輕人���,懂電商���,但對傳統家居文化了解有限����;而吳永忠則是老一輩手藝人,很想把自己的一身絕活通過商業手段傳承下去����。
于是����,吳永忠收下了這個“弟子”,把自己熟練掌握的榫卯工藝教授給設計師�����,讓他們通過產品設計把這門手藝��,通過淘寶傳播到千家萬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