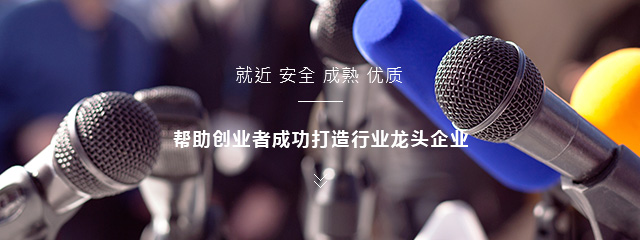摘 要: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,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家具中的一朵奇葩。家具總是伴隨社會的發(fā)展而發(fā)展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在長期的社會發(fā)展進程中逐漸形成了極具民族特色的家具風格。本文將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發(fā)展歷程劃分為濫觴及緩慢發(fā)展時期,肇始演進時期和興盛發(fā)達時期,深入分析三個時期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藝術(shù)特征、文化內(nèi)涵。
關(guān)鍵詞:藏式家具;西藏;佛教
1 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發(fā)展分期
何為傳統(tǒng),《辭海》解釋為:從歷史上沿傳下來的思想、文化、道德、風尚、藝術(shù)、制度以及行為方式等。它通常作為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被繼承下來,其中最穩(wěn)定的因素被固定化,并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(xiàn)出來。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是藏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發(fā)展進程中,立足本土文化,并積極地與外來文化交融而形成的,具有獨特的藝術(shù)特征、反映出強烈的民族特質(zhì)和蘊含濃厚的傳統(tǒng)文化內(nèi)涵等特點。
對于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發(fā)展歷程的劃分,現(xiàn)有學(xué)術(shù)成果主要以民族史學(xué)或社會史學(xué)的角度劃分,如在《藏式家具文化研究》一文中,基于藏族歷史的發(fā)展過程,將藏式家具劃分為四個階段:一是史前時期;二是雅礱部落、吐蕃王朝、分裂時期;三是藏傳佛教三大派執(zhí)政時期;四是西藏解放至今。這一劃分法存在主體錯位的問題,如以民族發(fā)展史或社會發(fā)展史代
替家具發(fā)展史的階段劃分,將因主體完全不同而致使階段劃分肯定不科學(xué)而出現(xiàn)偏差,由此導(dǎo)致各歷史時期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特點歸納出現(xiàn)偏差、移位等。
本文以藏族發(fā)展歷程為基礎(chǔ),緊扣家具主體,從家具本體的藝術(shù)、文化等特征對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進行劃分,似乎更為科學(xué)、客觀,具體劃分為濫觴及緩慢發(fā)展時期、肇始演進時期及興盛發(fā)達時期三個階段。
2 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濫觴及緩慢發(fā)展時期
石器時代至吐蕃王朝建立前,是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濫觴、緩慢發(fā)展時期。一統(tǒng)的國家尚未建立,氏族部落(部落小邦)林立、各自為政。經(jīng)濟上處于農(nóng)耕經(jīng)濟和畜牧經(jīng)濟的較低階段,外來文化影響十分有限,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藏地區(qū)家具的發(fā)展。具體表現(xiàn)為:雖隨著對木材質(zhì)性能認識的深入、加工工具的進步,這一時期的家具在形制上仍較為單一。在家具文化方面主要以苯教文化為主,裝飾內(nèi)容應(yīng)主要為自然景象、動物及圖騰崇拜符號等;由于生活方式的原因,以低矮家具為主。
由于歷史久遠、木材難以保存等原因,西藏地區(qū)家具的確切起源年代尚無定論,不過應(yīng)是與這一地區(qū)有人類造物文化同步。正如楊耀先生在其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一書中所說:人類遠在使用石器工具的年代里,就會使用自然石塊堆成原始家具的雛形“∏”,具備承具的功能。卡若文化遺址中建筑的卵石墻體顯示,新石器時期,西藏先民能熟練利用石材,家具極有可能濫觴于這一時期。
在人類社會中,自從有了蓋房子的活動期,就有了做家具活動。一般來說,建筑是表,家具是里。[1]家具作為建筑內(nèi)部空間環(huán)境不可或缺的要素,它總是伴隨著建筑的發(fā)展而發(fā)展的。據(jù)西藏卡若遺址發(fā)掘報告顯示,該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,文化層分為早、晚兩期,共發(fā)掘房屋遺址31處。在早期房屋遺址中出現(xiàn)了柱、椽木等建筑構(gòu)件,說明當時古人已學(xué)會了利用石器工具,如石斧、石錛對木材進行加工利用,加工木材制作家具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卡若文化遺址后期房屋建筑形式、構(gòu)件與前期大體相同。可以說,西藏地區(qū)家具在新石器時代發(fā)展極為緩慢,歷經(jīng)千余年。
石器時代可以說是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萌芽期,受加工工具所限,家具形態(tài)極為單一。
隨著青銅時代(青銅器與鐵器并存)的到來,金屬加工工具的出現(xiàn),西藏地區(qū)的家具發(fā)展呈現(xiàn)新的面貌,趨規(guī)整。
距今約4000年,相當于中原地區(qū)的夏代早期,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帶的曲貢遺址藏族先民已經(jīng)開始步入青銅時代(公元前1000年至吐蕃帝國)。距今2500-2000年,約相當于中原戰(zhàn)國秦漢之際,鐵器可能在這個時期已經(jīng)傳入西藏高原。曲貢遺址中出土的鐵柄銅鏡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。[2]
拉薩市曲貢遺址H12出土了一枚青銅箭鏃,距今年代為3500—3700年。經(jīng)檢測,該青銅鏃為銅錫合金,本地鑄造而成。西藏高原青銅器、鐵器的普遍出現(xiàn)是來自石構(gòu)墓葬。[3]這些器物雖大都為兵器、生產(chǎn)工具、飾件等,但其中一些器物已具備良好的木材加工的功能,如貢覺香貝石棺墓出土的銅刀,雙刃,刃部鋒利和德清永芝石棺墓中出土的青銅斧等。在阿里地區(qū)札達縣古墓出土過一把木梳,造型精巧、齒尖細密,只有金屬利器才能加工出如此光潔而整齊的梳齒。[4]可見,這一時期木材加工更趨精細。
按藏文古文獻記載,距今約2000多年的吐蕃第八代贊普布德貢加時期,人們已熟練掌握了冶煉金、銀、銅、鐵的技術(shù)。[5]這極大地促進了木材加工工具多樣化、精細化,家具的造型勢必更趨多樣,功能性有較大提升。
青銅時代至吐蕃王朝初期,這段時期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有了長足的發(fā)展。由于金屬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建筑構(gòu)件加工技術(shù)的豐富,受此影響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的形制趨多樣化、功能實用化,生活家具應(yīng)占主要部分,從考古發(fā)掘報告分析,不排除專門的宗教類家具的出現(xiàn)。
3 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肇始演進時期
吐蕃王朝時期,為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肇始演進時期。
公元七世紀初,吐蕃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先后兼并境內(nèi)諸部,統(tǒng)一全境,建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(quán)——吐蕃王朝。
松贊干布繼位后很長一段時間是文化大開放、大交融、大發(fā)展時期。佛教的傳入及其深入地影響社會生活各方面,同時,與尼泊爾、唐王朝等不同文化的深入交流,文化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空前繁榮。隨著與周圍政權(quán)的頻繁貿(mào)易、文化交流不斷深入,手工業(yè)、商業(yè)發(fā)展順速,達到一個新的高度。隨著本土的苯教文化與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不斷的沖突、矛盾中融合,對漢文化的吸收等,逐漸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態(tài)。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在開放、包容的文化氛圍中逐漸形成了制作技藝豐富、色彩明艷瑰麗、宗教意味濃郁、裝飾圖案寓意多元的藝術(shù)格調(diào),同時,家具文化的民族性在這一歷史時期確立。家具體系進一步完善,結(jié)構(gòu)藝術(shù)更為完善,高足家具很可能在這一時期出現(xiàn)。
對西藏地區(qū)家具藝術(shù)發(fā)展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佛教的引入和與包括唐王朝在內(nèi)的周邊政權(quán)的文化交流,這一時期的家具藝術(shù)迎來了空前的繁榮時代。
約621年,泥婆羅(今尼泊爾)赤尊公主入藏,自此揭開了佛教大規(guī)模進入吐蕃的序幕。入藏時,公主攜帶精美佛造像、法器、金銀器等物,不少匠人亦同期隨性,自此,尼泊爾高超的建筑技術(shù)傳入吐蕃,大昭寺所見建筑木雕裝飾手法、圖案帶有明顯印度、尼泊爾風格,隨即影響家具藝術(shù)等其他文化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。
貞觀十五年(641年),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,據(jù)藏史文書記載,文成公主攜帶有大批佛教經(jīng)典、醫(yī)學(xué)、工藝等方面的書籍,無數(shù)侍者隨行,其中包括不少工藝技術(shù)人員。《西藏王統(tǒng)記》中記載道:……工巧技藝制造術(shù),高超能令人稱羨,如此工藝六十法,如此賞賜我嬌女。……。在藏區(qū)流傳關(guān)于歌頌文成公主的民歌唱到:……,尊敬的文成公主,帶來手工藝五千種,打開了吐蕃工藝,繁榮昌盛的大門……。可見,工藝技術(shù)人員中應(yīng)有不少木工工藝匠人,因為文成公主入藏后興建的小昭寺帶有濃郁的漢式建筑風格,飛檐翹角、建筑木制構(gòu)件等。除此之外,在木質(zhì)建筑物上所刻人物、獸、禽等形象逼真、古樸、生動。鑿刻技術(shù)精細,大都采用雕刻法。[6]在此可斷定,在當時,成熟的雕刻技藝應(yīng)普遍用于家具制作中,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的加工技法。
中宗景龍四年(公元710年),藏王尺帶珠丹迎娶金城公主入藏,公主攜帶醫(yī)學(xué)、歷算和工藝書籍無數(shù),諸多工匠、雜役等專業(yè)人員隨行入藏,漢藏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繁榮。
文成公主、金城公主先后入藏極大地推動了吐蕃王朝文化、藝術(shù)的繁榮,其中也包括家具藝術(shù),不僅豐富了工藝手法,拓展了家具的結(jié)構(gòu)樣式,而且使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融入了漢地文化的因子,增加了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的文化維度,出現(xiàn)了漢地裝飾紋樣,如寶相花、饕餮紋、纏枝紋等。
佛教自吐蕃王朝初期傳入始,一直與本土宗教——苯教發(fā)生矛盾、沖突,在不斷的斗爭中相互影響、吸收從而日益興盛,松贊干布即位后,佛教正式立足并開始深入影響藏民的物質(zhì)生活和精神生活,西藏文化的向度就此更向。隨著百余座寺廟的營建,佛教對家具藝術(shù)方面的影響悄然深入,最終促進了西藏家具風格的形成。
首先,在造型方面,受藏傳佛教的影響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造型大多為長方形或正方形,呈現(xiàn)“中規(guī)中矩”的特點,體量較大而厚重,無論在視覺抑或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壓抑感,鉗制了人們的自由遐想。[7]需要指出的是,受藏傳佛教的影響,佛龕這一家具類型得到極大地發(fā)展。佛龕是專門供奉佛像的一類家具,也是藏傳佛教寺院最重要的家具之一,一般被打造成集木工、雕刻、彩繪、鑲嵌、貼近、涂漆等工藝于一體的家具精品。
其次,裝飾色彩方面,紅色、黃色、金色等色彩被賦予了濃郁的宗教含義。在藏傳佛教中,紅黃兩色代表崇高、代表圣潔、代表信仰,是僧人和信眾尊崇的顏色。(圖1)一些宮殿、寺廟的神殿、重要的佛堂外墻大多都是紅色,以示威嚴。在藏式家具裝飾中,紅色是主要色調(diào),運用最多,最為醒目。[8]黃色更是備受尊崇、意為脫俗,平常人家的建筑基本上沒有使用黃色的,只有寺廟、活佛的駐錫地和高僧大德的寓所才有資格“身披黃色的外衣”。金色在藏傳佛教中被賦予威懾天下,助長事業(yè)、增益行愿等含義。在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中,用于禮佛的家具中通常會使用金色,有的甚至通體包鎏金銅飾,如此以示敬畏。
最后,裝飾題材、紋樣更為豐富。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,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的裝飾題材、紋樣更多地以自然、苯教宗教為主。受佛教影響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題材、紋樣更加廣泛,都忠實地刻畫這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、民族品格與精神追求。從現(xiàn)存歷史家具實物分析,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佛教題材主要包括:動物紋,如大鵬金翅鳥、雪獅、吐寶鼠鼬等;植物紋樣,如蓮花;佛教人物,如轉(zhuǎn)輪王;組合紋樣,如八寶紋樣、輪轉(zhuǎn)王七珍等;器物紋,如金剛杵;文字紋,如“卍”字等等。(圖2)
隨著朗達瑪滅佛運動的發(fā)生,一統(tǒng)的吐蕃王朝逐漸全面崩塌。從此內(nèi)亂四起、大小政權(quán)割據(jù),這一局面持續(xù)約400年之久,這一時期的文化、藝術(shù)幾乎處于停滯狀態(tài)。
宋代朝廷未能與存在于原吐蕃中心地區(qū)的各地方勢力發(fā)生聯(lián)系,只是與河湟、西川各藏族部落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上存在一定的聯(lián)系。由于政治、軍事上的需要,宋朝對這些吐蕃部落采取“羈縻懷柔”政策,漢藏工藝美術(shù)通過賞賜、互市等方式相互交流。[9]對西藏地區(qū)的文化影響力雖遠不及唐王朝,在文化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,兩宋時期漢地文化仍有一定的影響。布達拉宮所藏南宋《不動明王像》緙絲唐卡上纏枝蓮花紋,從形態(tài)到配色,明顯來源于宋代絲綢紋樣,充滿自然氣息,寫實感十足。[10]結(jié)合現(xiàn)存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實物比對分析,自然花卉寫實性畫法的裝飾手法應(yīng)受宋代花鳥畫繪畫藝術(shù)的影響。
4 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興盛發(fā)達時期
元明清時期,是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興盛發(fā)達時期。從元朝始,西藏便始終納入中國的版圖,多民族融合的國家觀念逐漸形成。不同歷史時期,中央政權(quán)以不同制度、手段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,同時在商貿(mào)、文化方面的交流較以往歷史時期更加深入、廣泛。不論宮廷工藝美術(shù)抑或民間工藝美術(shù)均源源不斷地在西藏地區(qū)被廣泛傳播而接受,漢藏文化藝術(shù)交流達到空前的高度,內(nèi)地文化藝術(shù)對西藏文化藝術(shù)、社會生活的影響大幅向前推進、深入。不論宮廷工藝美術(shù)抑或民間工藝美術(shù)均源源不斷地在西藏地區(qū)被廣泛傳播而接受,漢藏文化藝術(shù)交流達到空前的高度,內(nèi)地文化藝術(shù)對西藏文化藝術(shù)、社會生活的影響大幅向前推進、深入。在家具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,漢文化較之前任何歷史時期更加深入,世俗吉祥文化融入其中,裝飾構(gòu)圖形式更為豐富。
13世紀中期,元朝統(tǒng)一西藏,將其納入中央王朝直接統(tǒng)治之下,結(jié)束西藏地區(qū)長期割據(jù)局面,社會漸趨穩(wěn)定,生產(chǎn)力得到快速發(fā)展,經(jīng)濟、文化在原先的基礎(chǔ)上進一步繁榮。
由于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封建農(nóng)奴制度,世俗民戶被世俗領(lǐng)主占有,寺屬民戶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領(lǐng)袖占有的奴隸,生產(chǎn)資料和社會資源集中于領(lǐng)主們手中,兩類民戶皆無生產(chǎn)資料和人身自由。[11]這一農(nóng)奴制度嚴重的限制了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多元化的發(fā)展空間而出現(xiàn)兩極分化,主要以宗教類家具為主,如佛龕、經(jīng)桌等,它們往往制作精美,而民俗家具發(fā)展極為緩慢且較為簡陋。
也許由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,在造型和裝飾手法方面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出現(xiàn)了蒙古族傳統(tǒng)家具的某些特征。箱柜類家具包裹皮革或動物毛皮,以牛、羊居多,呈現(xiàn)自然特性及質(zhì)感效果。由于游牧遷徙的生活方式,為保證在搬運過程中的結(jié)實耐用,箱類家具通常在端角、兩面相交的棱邊處用鐵制件加以固定。[12]在裝飾圖案方面,甚至出現(xiàn)了“蒙人馭虎”的圖案。
下及明清時期,兩朝對西藏的統(tǒng)治均有一套完備的行政、軍事管理制度。通過朝貢封賞制度和“茶馬互市”等加強了對藏區(qū)的管理和文化聯(lián)系、交流。內(nèi)地大量工藝美術(shù)的輸入,對藏族人民的審美觀念產(chǎn)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,對促進藏族文化藝術(shù)的發(fā)展、繁榮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。清中后期隨著格魯教派的興盛,佛教美術(shù)普及到民間。民間的經(jīng)房和家庭經(jīng)房的出現(xiàn),宗教類家具在民間興起,佛龕、經(jīng)桌等流行整個社會,與民間納祥祝福的世俗題材結(jié)合,影響到民俗家具。[13]
從現(xiàn)存實物分析,明清時期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受內(nèi)地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(xiàn)在裝飾藝術(shù)方面,裝飾題材更為廣泛,一些世俗題材用于裝飾,漢地的吉祥文化滲入其中。動物紋以龍、鳳、鶴、鹿居多;植物紋有菊、牡丹、竹等;文字紋主要有壽字;人物紋以童子的形象為主。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,隨著漢、藏優(yōu)秀文化的不斷交流和融合,諸多漢民族文化特色的圖形、圖案被運用于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中,并得到藏民的喜愛,如陰陽八卦圖和道教八仙,從中亦能管窺漢、藏之間的宗教交流、融合。[14]此外,漢民族傳統(tǒng)的二方連續(xù)、四方連續(xù)及開光的構(gòu)圖形式也常見于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中,充分表明家具這種與生活密切相關(guān)的造物,隨著生活環(huán)境的變化自覺與不自覺地改變的歷史規(guī)律。
西藏和平解放后,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,西藏社會各領(lǐng)域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傳統(tǒng)家具迎來了新的發(fā)展機遇。在全新的歷史時期,西藏傳統(tǒng)家具如何煥發(fā)新的發(fā)展活力,以適應(yīng)市場需求,值得深入研究。
[基金項目: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(xué)研究青年基金項目:中國藏族傳統(tǒng)家具裝飾藝術(shù)研究,項目編號:18YJC760024]
作者簡介 :胡名芙(1978- ),男,漢族,江西吉安人,江西財經(jīng)大學(xué)講師,碩士,主要從事中外家具設(shè)計史及設(shè)計理論研究,E-mail:
[email protected]通信地址:江西南昌 江西財經(jīng)大學(xué)藝術(shù)學(xué)院 330013;胡名芙,15070933457